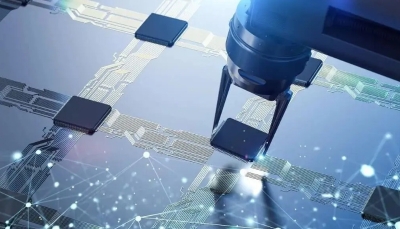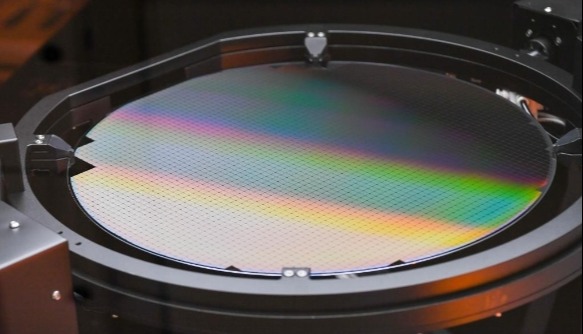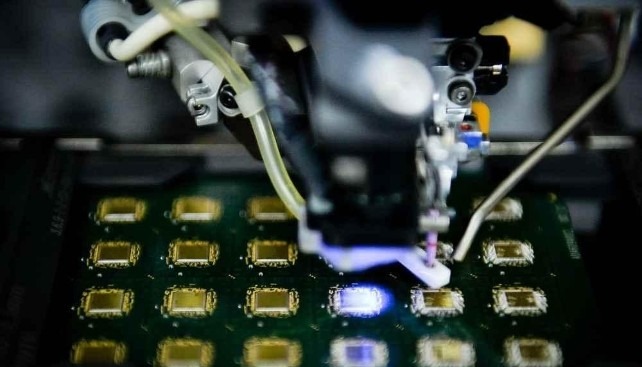特朗普為何“改革”拜登時代AI管制政策,影響如何?香港新聞網5月15日電 (記者 王少喆)美國商務部13日宣佈,撤銷拜登政府時期制定的《人工智能擴散出口管制框架》,該政策原本將於5月15日生效。拜登政府的這一政策,嚴格限制了美國AI芯片企業的出口,曾經受到英偉達、甲骨文等美國企業的強烈反對。不過,特朗普並不準備取消對美國AI芯片出口的限制,而是希望用一個新的、“更聰明”的框架來替代拜登的做法。美方還明確提出,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華為昇騰AI晶片均違反美國的出口管制。特朗普政府的這一政策“轉彎”有什麼背景?這對中國的AI科技發展會有什麼影響。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就此書面採訪了科技戰略專家蘇世偉先生。採訪全文如下: 1、 特朗普政府這次取消拜登時期制定的AI芯片管制政策,背景是什麼?是否主要是受到了英偉達等AI芯片商的游說? 答:拜登時期推出的《人工智能擴散出口管制框架》,目的在於限制美國先進AI芯片的出口,以防止中國、俄羅斯等對手國家獲取關鍵技術。拜登政府的“AI擴散規則”將全球國家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美國的親密盟友,可無限制獲取AI芯片;第二類為其他國家,受限於芯片數量;第三類為中國、俄羅斯等對手國家,幾乎被完全禁止獲取。 本來,特朗普政府就一直認為該規則過於複雜和官僚,可能阻礙美國的創新能力和全球競爭力。事實上,英偉達佔據AI全球芯片市場份額約為90%。該公司認為 “AI擴散規則”將限制其全球業務發展,尤其是在中東等新興市場。英偉達的持續抗爭,目前已取得重要進展。在特朗普訪問沙特期間,黃仁勛與其共同出席了投資峰會,強調了放寬出口限制對美國科技企業的重要性。 中國DeepSeek的橫空出世,使美國業界看到,AI芯片的研發進程不是靠技術管制就能阻止的。埃隆•馬斯克和AMD首席執行官蘇姿豐等科技領袖,積極參與了廢除AI科技禁令的相關活動,顯示出科技行業對放寬出口限制的廣泛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調整被視為對相關企業訴求的積極回應。 在上述背景下,英偉達等AI芯片巨頭的游說是關鍵推動因素之一。2025年,拜登政府的管制政策已導致英偉達對華AI芯片銷售額較2023年下降超50%(從25%占比降至不足10%),AMD、英特爾等企業同樣面臨中國市場份額被華為昇騰、寒武紀等國產芯片擠壓。AI企業通過美國半導體協會(SIA)向政府施壓,警告“失去中國市場將永久性削弱美國技術領導地位”。中國市場與美國技術領導地位存在如此緊密聯繫,這是清醒的認識。 另一方面,從特朗普履行競選前的承諾來看,也該回報有功之臣了。2024年大選中,英偉達、高通等企業向共和黨捐贈超千萬美元,重點支持亞利桑那、得克薩斯等半導體產業集中州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勝選後,需兌現對“金主”的政策回報。 同時,對中國的技術遏制失效,也迫使特朗普改變政策。中國在2024-2025年實現昇騰910B芯片量產(性能接近A100),中芯國際突破7nm DUV自主工藝,拜登的“制程封鎖”策略已實質性破產。特朗普團隊評估認為,繼續管制反而加速中國去美化,不如通過“中端芯片傾銷”延緩中國高端研發。 還有,特朗普將芯片管制視為“交易籌碼”,以放寬限制換取中國在貿易、台灣問題、俄烏衝突等領域的讓步,延續其“美國優先”的交易式外交風格。從國內來看,亞利桑那州(台積電工廠)、俄亥俄州(英特爾新廠)等地的數萬個就業崗位直接依賴對華芯片出口,共和黨需在2026年中期選舉前鞏固這些關鍵州的選民支持。這是特朗普的票倉,大意不得。 儘管美國國防部、情報機構及部分共和黨議員(如盧比奧)強烈反對放寬管制,認為AI芯片可能被轉用於中國軍事AI(如高超音速武器軌跡計算、無人機群協同算法)。但特朗普為平衡利益,可能采取“分級放開”策略(如允許出售A800級別芯片,但繼續封鎖A100/H100)。 總之,英偉達等企業的游說為政策轉向提供了直接推力,但更深層原因是:技術封鎖失效,中國自主替代倒逼美國調整策略;經濟現實壓力,半導體產業萎縮威脅美國全球領導地位; 政治交易需求,芯片成為對華博弈的靈活籌碼。特朗普政府取消對華AI芯片管制,本質上是企業利益、戰略調整、國內政治博弈的綜合結果。
美國總統特朗普 圖源:新華社 2、 特朗普政府準備取而代之的管制政策,會是什麼樣的?其中對華為芯片的限制,是出於什麼目的? 答:特朗普政府并非完全放棄AI芯片出口管制,而是計劃以“更靈活、目標更精準”的方式取而代之,新政策的核心方向可能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簡化國家分類系統。拜登政府的“AI擴散規則”按國家分三級,引發企業不滿。特朗普政府計劃取消這種廣泛、複雜的分類方式,轉為基於實體和項目的“黑名單”管理,而非整國封鎖。這將使美國企業在“友好國家”更自由地開展業務。 其次, 聚焦“高風險實體”而非國家整體。新政策將重點監控“有軍事背景或技術轉移風險的公司/機構”,如中科曙光、寒武紀、華為等,而非限制整個中國市場。這樣可以更有效避免“誤傷”民用或中立用途的合作夥伴。可以按算力(TOPS)、制程(7nm/5nm)等指標將AI芯片分為“民用級”(如英偉達A800)和“軍用級”(如A100/H100),僅對後者維持嚴格出口限制,前者允許對華銷售,但需企業承諾“不用於軍事終端”。 再次,開放中東及其他“可信”市場的合作。特朗普政府允許阿聯酋每年進口高達50萬顆先進AI芯片,顯示出其新政策會更傾向於與中東、東南亞等地區深化科技合作,以抗衡中國在全球的技術影響力。威脅制裁任何向中國轉售高端AI芯片的第三國企業,迫使其遵守美國管制規則;要求台積電、三星等非美系代工廠簽署協議,禁止利用美國設備(如應用材料刻蝕機)為中國企業生產等效替代芯片。 最後,根據中國技術突破情況(如華為昇騰芯片迭代),每年更新管制清單,確保美國始終領先1-2代技術。放寬芯片管制的同時,要求中國取消對美國雲計算企業(如AWS、微軟Azure)的在華運營限制;降低美資半導體企業(如英特爾、高通)在華合資公司的股比門檻;承諾不補貼國產AI芯片(如華為昇騰、寒武紀)的“價格傾銷”。還可以通過關稅杠桿:美方認為中國違反協議,可對AI芯片加征懲罰性關稅(如30%),而非直接禁售。 特朗普政府對華為AI芯片的限制,出於以下目的: 第一, 防止中國軍民融合背景下的技術通用。華為是中國“軍民融合”政策的重要執行者之一,其AI芯片(如Ascend系列)已廣泛用於安防、監控、軍事模擬等領域。特朗普政府擔心,若不限制對華為芯片的接入和擴散,將間接提升中國的軍事技術能力,特別是在圖像識別、目標追蹤等AI軍用場景中。 第二、打擊華為的全球生態擴張計劃。華為正試圖通過AI芯片與雲服務(如昇騰AI + 華為雲)構建自己的全球技術生態。如果其芯片廣泛用於中東、非洲等新興市場,將形成與英偉達、AMD等美國公司的競爭格局。限制華為,就是阻止中國科技企業在發展中國家建立“數字依賴”。 第三,向全球企業施壓,排除華為芯片選項。美國警告全球公司,如使用華為Ascend系列芯片,可能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規。這種制裁模式,力圖打擊華為國際市場份額,使其成為“高風險合作對象”。 總的看,特朗普政府的新管制政策“表層放鬆、底層收緊”。放寬中低端芯片出口,緩解美企短期營收壓力;通過技術追蹤、分級封鎖和交易杠桿,確保中國難以突破軍事AI關鍵領域。特朗普政府對華為實施AI芯片限制,并非單一動機驅動,而是戰略遏制、技術壓制、經濟競爭、政治博弈的混合產物。 3、 新政策的影響會是怎麼樣的?對中國AI科技的發展能否減輕束縛? 答:特朗普政府的新AI芯片出口管制政策,將對全球AI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對中國AI科技發展的束縛短期內可能部分緩解,但長期挑戰仍存。 一是美國對中國中低端芯片供應恢復。若特朗普政府允許中端AI芯片(如英偉達A800/H800)對華出口,中國雲計算、自動駕駛等民用領域企業可快速補充算力資源,緩解因拜登時期全面封鎖導致的短期算力缺口。例如,百度、騰訊等企業的AI模型訓練進度可能加速。 二是降低國產替代成本壓力。華為昇騰、寒武紀等國產芯片企業可暫時減少“倉促替代”的投入,轉而通過技術吸收優化自主產品。例如,華為可采購A800芯片進行逆向工程,提升昇騰910B的架構設計效率。 三是技術自主化加速,中芯國際聯合上海微電子實現14nm DUV光刻機自主化,2027年或量產7nm昇騰芯片。AI技術生態重構,華為的MindSpore框架在中國市占率從2023年的15%升至2025年的40%,將來可能逐步替代目前常用的TensorFlow/PyTorch框架。 四是提供國際技術合作窗口期。美國放寬部分管制後,歐洲、日韓企業可能重啟對華技術合作(如荷蘭ASML對中芯國際供應舊款DUV光刻機),為中國芯片製造設備升級提供過渡期支持。 特朗普的AI新政,儘管暫時能緩解中國的AI研發壓力,但并沒有真正減輕束縛。 美國對中國高端芯片持續進行封鎖。特朗普政府可能維持對高端AI芯片(如A100/H100)及製造設備(EUV光刻機)的嚴格限制,導致中國在大模型訓練、超算升級等領域仍受制於人。例如,中國“神威•太湖之光”超算若無法獲得最新HBM內存技術,算力升級將受阻。華為、寒武紀等企業面臨高端芯片斷供,自動駕駛、超算等項目進度延遲(如百度自動駕駛系統Apollo需重新適配國產芯片)。 中國技術依賴風險還在。若中國企業過度依賴美國中端芯片供應,可能延緩自主創新動力,陷入“進口替代惰性”。例如,部分AI企業或傾向於直接采購英偉達A800,而非投入高成本研發國產等效產品。中小AI企業因算力成本上漲(國產芯片價格比英偉達高30%),可能引發行業洗牌。 美國的供應鏈監控與次級制裁,對中國還是壓力山大。特朗普可能強化對芯片流向的追蹤(如植入硬件監控模塊),并威脅制裁第三國企業(如台積電為華為代工),導致中國技術突圍路徑進一步收窄。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調整可能為中國AI科技發展提供短暫喘息期,但無法根本解除技術遏制,對中國來說,是鬆綁表象下的持久戰。中國需要利用進口芯片填補算力缺口,維持AI應用層創新;加速核心技術攻關,突破“卡脖子”環節;構建獨立技術生態,爭奪全球AI標準話語權。 中國AI發展的束縛能否徹底解除,取決於自主創新速度與美國政策耐力的賽跑。若中國在5-10年內實現EDA工具、光刻機、AI框架全鏈條突破,特朗普的管制政策將淪為“紙老虎”;反之,則可能陷入“溫水煮青蛙”式的技術依賴困局。(完) 【編輯:王少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