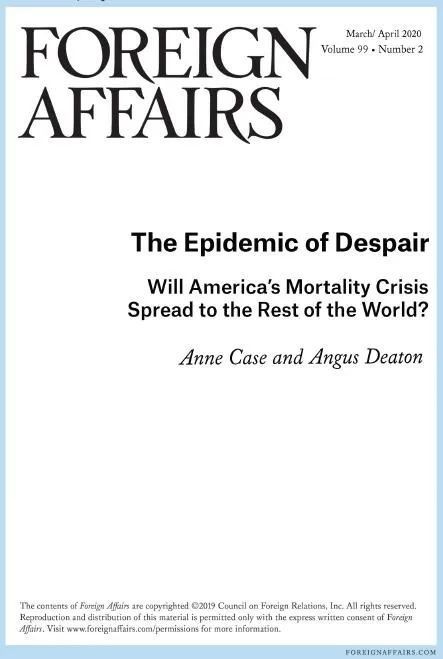諾獎得主解析:芬太尼在美泛濫,為何歐洲沒有?香港新聞網5月15日電 《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發佈後,全球高度關注雙方高層會談的具體事宜。近日,有法新社記者提問有關芬太尼問題的談判安排,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芬太尼是美國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責任在美國自身”。這牽出了特朗普在今年2月初和3月初以“芬太尼危機”為名,兩次宣布對華額外加征共計20%全面關稅的單邊主義行為,對此外交部剛剛發佈聲明,表示并未撤銷“芬太尼關稅”的有關反制措施。那麼,美國社會內部的芬太尼危機究竟是如何演化的? 下文指出,20世紀後期,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原本持續上升,但最近幾十年卻掉頭連續下降。這在美國工人階級中尤為顯著,自殺、濫用成癮性藥物、酒精性肝病成為致死主因。伴隨著日益增長的絕望情緒,芬太尼等阿片類止痛藥愈發泛濫。大規模的“海洛因合法化”雖引發了超高致死率,但製藥公司通過政治游說,規避了政府的監管強化。如今,美國醫療服務市場上的三大主體(醫藥企業、醫療機構和保險機構)已構成“旨在增進醫療供給者財富”的隱性聯盟。他們具備強大的市場主導能力,并通過政商聯盟實現了變相壟斷和尋租,導致醫療價格不斷上升。 下文還指出,美國擁有世界最發達的醫療技術,但其獨有的醫療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對工人階級并不友好。一方面,產業結構調整加劇了“低技能”人群失業,而醫保由企業承擔的現實,導致用工崗位進一步縮減,普通美國人陷入到藥物濫用和失業的泥潭之中。另一方面,伴隨家庭、社會、國家福利等傳統保障網絡的衰落,醫療供給者聯盟卻逐漸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底層美國人愈發弱勢。這意味著,以芬太尼為由打壓中國,可謂是特朗普轉移內部矛盾,向底層選民投喂的一粒止痛藥。 本文編譯自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原題為《The Epidemic of Despair: Will America’s Mortality Crisis 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作者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安妮·凱斯,以及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本文主要關注美歐的健康問題,但其折射的全球性的社會結構之變、醫療市場化等問題,也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當然,由於美方立場、議題設置等原因,本文也可能僅僅反映局部信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編譯正文如下:
原文封面。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一直在遭受“絕望之死”(death of despair)這種流行病(epidemic)的困擾。這個術語創造於2015年,旨在形容由藥物過量、酒精性肝病或自殺造成的死亡。如今,“絕望之死”的人數不斷上升,已成無可阻擋之勢,連同長期以來因心臟病死亡人數的再度回升,最終呈現出一個驚人趨勢:從2015年到2017年,剛出生美國人的預期壽命連續三年下降。上一次美國出現這種情況,還是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大流感(譯者注:Great Influenza epidemic,1918年1月-1920年4月)。 二十世紀時,美國在降低死亡率和提高預期壽命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許多重要的健康改善措施就起源於美國:如禁煙和推廣使用抗高血壓藥,降低了心臟病死亡率;發展新生兒重症監護室,降低了嬰兒死亡率。此外,隨著知識、藥物和技術的傳播,全球其他地區的死亡率也隨之下降。 現在,美國可能正帶領西方國家走向相反的方向。美國人的“絕望之死”是否將蔓延到其他發達國家? 是,也不是。一方面,數據分析表明,美國的糟糕情況有一定的例外性,尤其當涉及到“絕望之死”時,美國與其說是風向標,不如說是對其他國家的警示。另一方面,我們也確實有理由感到擔憂,因為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和英國,死於藥物過量、酒精和自殺的人數已在逐漸上升。儘管這些國家擁有更好的醫療保健系統,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絡,以及比美國更好的阿片類藥物管控,但他們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公民,同樣面臨著全球化、工作外包和自動化的無情威脅。經濟威脅正侵蝕著整個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生活方式,并推動美國“絕望之死”的危機。 ▍“絕望之死,美國的病” 美國的死亡率在二十世紀後四分之三的時間內持續下降,直到90年代末,這一進程放緩,并很快出現了逆轉。 預期壽命下降的一個主要原因是25至64歲間的中年人死亡率不斷上升,而增長最快速的死亡原因,是意外中毒(幾乎總是來自藥物過量)、酒精性肝病和自殺。藥物過量在三種“絕望之死”中最為普遍,自2000年以來有超過70萬人死於此因,2017年死於藥物過量的美國人達到7萬人。同年,絕望之死的總人數為15.8萬人,超過1995年艾滋病高峰之年的死亡人數,也超過了在越南戰爭中的死亡人數,相當於這一年內每天有三架滿載的波音737飛機從空中墜落。 2000年以來,“絕望之死”的總人數超過了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死亡人數。自1999年以來,美國的自殺率上升了三分之一,如今每年的自殺人數超過了公路死亡人數,是謀殺死亡人數的2.5倍。 較近期出生的美國人,在人生任何年齡段死於毒品、酒精或自殺的風險都遠高於之前的人群,而他們死亡率隨年齡增長的上升趨勢也更快。這種死亡率的快速上升的趨勢同時適用於男性和女性,但女性“絕望之死”的基礎比率更低。 在2013年前,非裔美國人“絕望之死”的增長趨勢并不突出。由於心臟病防治的進展突然放緩,以及2013年後芬太尼等阿片類藥物在街頭蔓延,非裔美國人的死亡人數迅速增加。在此之前,“絕望之死”的流行主要局限於非西班牙裔的美國白人。 “絕望之死”的美國人幾乎都沒有獲得四年制的大學學位,本科學位似乎能抵禦因毒品、酒精和自殺的死亡人數增加。過去,人們總認為自殺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的一種痛苦。事實上,對於1945年以前出生的美國人來說,受教育程度較高和較低的人的自殺率幾乎相同。然而,對於二十世紀後期出生的人來說,教育程度不同人群的自殺率有明顯差異:例如,對於1970年出生的美國人,非大學畢業生的自殺率是大學畢業生的兩倍以上。大約三分之二的非西班牙裔美國白人沒有學士學位,占成年人口的42%,正是這個群體最容易陷入“絕望之死”。 ▍大洋彼岸的情況 美國并不完全是唯一在經歷“絕望之死”的國家。這三類死亡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但大多數富裕國家還沒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但英語國家是個例外。自2000年以來,儘管英語發達國家的絕望之死比率仍然比美國低很多,但已經出現明顯上升趨勢,并且三類死亡的增長趨勢有所不同。 英國是一個有參考價值的例子。自1990年以來,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絕望之死”一直在穩步上升。在1990年代和本世紀初,與酒精有關的肝病死亡率迎來高潮,但近年來已經消退。自2000年以來,自殺率有所上升,但大部分“絕望之死”的增長來自於藥物過量。對於英國中年人而言,如今“絕望之死”比心臟病的死亡率更常見,但英格蘭和威爾士仍然不到美國的一半。(整個英國的一個黑點是蘇格蘭,由於非法藥物的使用,那里因藥物過量而死的比率幾乎達到了美國水平)。 在美國以外的國家,一般沒有將教育水平與絕望之死聯繫起來的數據。然而,有幾項研究表明,包括英國在內的幾個歐洲國家中,不同教育水平人群之間的死亡率差距一直在縮小,這與美國近年來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如今,美國自殺率攀升過高,已遠遠甩開其他西方國家,而進入到東歐國家和前蘇聯在內的高自殺率群體中。 出生時預期壽命的趨勢,也揭示了美國與其他富裕國家的不同之處。2015年,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導致11個歐洲國家的預期壽命有所下降:由於當年的流感疫苗與病毒的匹配度不高,導致許多老人死亡。除此之外,整個歐洲大陸的死亡率上升趨勢逐步放緩。相比之下,英國的情況更加糟糕,其長期以來的預期壽命增長已經趨於平穩。在英國和北歐大部分地區,老年人死亡率的增加,或死亡率的下降趨勢放緩。 美歐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因為中年人快速增長死亡率是最大變量。相比之下,美國65歲以上的人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不過,現在已有跡象表明,仍然被認為是“最年輕的老年美國人”(65至69歲)有關毒品、酒精和自殺造成的死亡率正在快速增加。 ▍工人階級的挽歌 是什麼造成了美國人的“絕望之死”?無論是當下還是未來,這些因素是否將在其他國家產生同樣影響? 我們認為,美國的白人工人階級遭受了長期、緩慢的損害。工資的下降和好工作的匱乏已經動搖了美國工人階級生活的基本制度,包括婚姻、教堂和社區。很大程度上,結婚率的減少,導致四年制大學以下學歷者中絕望之死的流行:1980年至2018年期間,40歲群體的結婚率下降了50%。 由於工資較低,低教育程度男性的結婚機會更少,這也產生了“連續同居”的現象(serial cohabitation,譯者注:擁有多段婚前同居關係),很多人最終沒有進入婚姻狀態。在此情況,更多低教育程度的白人母親沒有結婚而生下子女,而父親大概率會與孩子分開,導致母子沒有穩定的家庭支柱和生活環境。工資、工作質量和數量、結婚率和社區生活的下降,是絕望誕生并蔓延的核心,激發了自殺和其他自我傷害,如酒精和藥物濫用。 2008年金融危機後開始的大衰退,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造成了很多痛苦,但這并不是引發美國工人階級“絕望的瘟疫”的原因。在經濟衰退開始之前,有關的死亡人數早已上升,并在2009年經濟衰退結束後繼續保持這種趨勢。這種流行病的真正根源,是1970年左右開始的長期萎靡不振:彼時,美國的經濟增長放緩,不平等開始飆升,年輕工人們意識到他們永遠無法獲得像其他(上大學)同齡人那樣的機會和地位,而那些沒有高級技能的工人則受到更大衝擊。 在美國,男性工資的中位數自此停滯不前。在一些歐洲國家,這種現象曾短暫出現,但并未形成長期的社會影響。過去20年里,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內的西方發達國際經濟和工資增長緩慢,但與美國最接近的是英國——那里的工資中位數或平均收入已經超過十年沒有增長,這是自工業革命以來該國工資停滯的最長時期。即使如此,相比美國半個世紀以來工資停滯和下降,英國也相形見絀。 美國和歐洲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後者有發達的社會支持系統,可以消減或扭轉勞動力市場變化的最壞影響。例如,在英國,1994年至2015年期間,最貧窮10%家庭的收入增長比最富裕10%家庭的收入增長要慢得多。然而,由於英國福利國家的再分配機制,稅後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在人口的各個部分大致相同。相反,在社會安全網更受限的美國,這種情況沒有發生。例如,在1979年至2007年期間,美國最貧窮的20%家庭的稅後收入和福利增長了18%,財富在80%至99%之間的富裕家庭則增長了65%,最富裕1%家庭則增長了275%。在這一時期,稅收和轉移支付制度對較貧窮的美國人來說失效了。 同樣,歐洲也沒有經歷美國所展示的那種婚姻破裂的情況。在歐洲,夫妻非婚同居很常見,但那里的同居更接近於婚姻。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男人和女人中經常出現“連續同居”現象,其中許多人會多次非婚生育,而這種情況在大西洋彼岸就要少得多。 ▍更多的錢,更多的問題 美國的另一個特有因素,極大地促進了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空洞化:美國醫療保健系統的巨大成本。美國的醫療保健支出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8%。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排名第二的是瑞士(12%),英國是10%,而加拿大是11%。然而,美國人的巨額支出并沒有換來很多健康方面的好處。美國人的預期壽命低於任何其他富裕國家,發病率和健康水平更為糟糕,而且數百萬人沒有醫療保險。 關鍵問題是,不僅美國醫療系統對健康的促進作用相當之小,而且它對經濟的危害是如此之大。如果美國將其醫療保健支出的百分比降低到瑞士的水平,它將節省6%的國民生產總值——每年超過1萬億美元,也就是說能為每個美國家庭每年節省約8600美元。這方面節省的費用就將達到軍事開支的180%。如今,醫療保健方面的浪費性支出已經是美國經濟體系的癌症(沃倫·巴菲特稱其對美國企業的影響就像“蛀蟲”一樣)。 這一費用增加了聯邦和州政府的赤字,并消耗了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的資源。如果美國工人不需要支付這筆巨大的額外費用,他們今天的生活會好得多。是的,醫療保健行業創造了就業機會,帶來工資收入,為醫藥公司的股東創造了利潤和分紅——但是,這些個別群體獲得收入的代價,是整個社會的浪費。被醫療保健行業吞噬的資源可以更好地用於其他方面,如改善教育,投資研發,以及修建道路、橋樑、機場和鐵路。 在這種美國醫療制度下,較低技術水平的工人受損最嚴重。美國是獨一無二的由雇主負責員工醫保的發達國家,擁有50名雇員或以上的公司必須提供健康保險。2018年,家庭保單的年平均費用為20,000美元。對於雇主來說,這就是工資一樣的勞動力成本,他們并不會關心這個成本究竟是通過工資、醫保或其他福利的形式在體現。隨著醫療保健成本不可阻擋的上升,必然會損害美國的就業和工資增長。 例如,對於年薪15萬美元的高技能工人,公司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健康保險費用;但對於低技能和低工資的工人,健康保險費用可能就是最終雇傭決定的破壞者。美國公司會試圖弄清楚,沒有這個工人是否可行,或者可否將工作外包給正在蓬勃發展的勞務派遣公司。在歐洲,各地的醫療保健越來越昂貴,外包業務也在迅速增長,但因為醫療費用不由雇主承擔的,因此醫療費用變動與工資和就業率的關聯并不明顯——高昂的醫療費用并沒有導致加拿大和歐洲公司削減崗位。 如果美國的醫療保健不是如此昂貴,那麼通過雇主提供醫療保健就不會成為一種壓力。隨著社會越來越富裕,將更多的國民收入用於延長生命和減少痛苦本來是有意義的事情,例如癌症死亡率的降低就是現代醫學的成功故事之一。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醫療支出都能產生預期的好處,但美國整個醫療系統的高昂成本阻礙了整個經濟的發展。相比其他發達國家,美國并沒有控制新藥或療法的價格,而醫療保健部門(包括醫生、設備製造商、醫院和製藥公司)已經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醫療保健行業相關每一位議員背後,都有至少五名說客。雖然歐洲也允許代表醫療保健公司的游說活動,但其規模與美國相比實在相形見絀。 在製藥公司擁有巨大政治影響力的環境下,美國對阿片類藥物的監管和控制失敗,并導致其廣泛流行。自1090年代末以來,伴隨著死亡率的上升,其他發病率也在上升:自我報告的疼痛、殘疾、社交困難和無法工作的情況全面增加。製藥公司及其經銷商利用這種日益增長的絕望情緒,廣泛推廣奧施康定(OxyContin)等阿片類止痛藥。在美國,這種合法藥物本質上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官方批准的海洛因毒品。 (譯者注:“阿片類藥物”,Opioid,包括從罌粟籽中提取的化合物以及具有類似性質的半合成和合成化合物,這些化合物可以與大腦中的阿片受體相互作用。阿片類藥物通常用於鎮痛,包括嗎啡、芬太尼和曲馬多等藥物。阿片類藥物的非醫療使用、長期使用、濫用和在沒有醫療監督的情況下使用會導致阿片類藥物依賴和其它健康問題。在全球範圍內,約有50萬人死於吸毒。其中,超過70%的死亡與阿片類藥物有關,超過30%的死亡由藥物過量引起。在美國,2010年至2018年期間死於阿片類藥物過量的人數增加了120%,2018年美國三分之二與阿片類藥物過量有關的死亡涉及合成阿片類藥物,包括芬太尼及其類似物。在全球新冠大流行期間,美國報告發生的吸毒過量死亡人數進一步大幅上升,主要是因為涉及合成阿片類藥物的用藥過量死亡人數迅速增加。) 1999年至2018年期間,有20多萬美國人死於處方阿片類藥物過量。隨著這些藥物造成的傷害不斷增加,醫生不再輕易開出處方,又為非法藥物打開了缺口:海洛因和芬太尼,并且後者的致命性更高。當社會混亂,并且生活失去意義時,就給了這些藥物滲入社會的可乘之機,并且進一步加劇了自殺和與酒精有關的死亡。 美國大規模的“海洛因合法化”本不應該發生,而且這個現象在歐洲也沒有發生。在歐洲,奧施康定等止痛藥也是合法的,但對它們的使用主要局限於醫院,并且醫院專門用於治療手術後立即出現的疼痛(例如,在髖關節或膝關節置換術後)。相比之下,在美國,一般醫生和牙醫也在大量開出這些藥物,以至於在2010年,向公眾開出的阿片類藥物足以讓每個美國成年人吃上一個月。藥品經銷商充斥著市場,有時會向只有幾百名居民的城鎮的藥店寄送數以百萬計的藥片。 當緝毒局試圖對這種“毒品”進行管制時,國會議員施加壓力,要求撤換負責的特工。國會甚至在2016年通過了一項法案,使對阿片類藥物的管控更難執行。1990年代中期,強生的一家子公司在塔斯馬尼亞(譯者注:Tasmania,澳大利亞唯一的海島州)種植罌粟,以提供阿片類藥物的原料,并避開國際麻醉品管制的漏洞。此後,說客們成功地阻止了美國國防部填補此漏洞的嘗試。根據法庭文件,自1995年奧施康定獲批以來,擁有普渡製藥的薩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累計通過銷售該藥物獲得了110億至120億美元的利潤。與美國不同,歐洲國家尚未允許製藥公司“為錢殺人”。 ▍遏制“絕望之死”的瘟疫 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能够顯著遏制“絕望之死”的瘟疫,并結束美國作為發達國家中“異類”的地位。在醫療保健方面,美國需要一個像英國國家健康和護理卓越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那樣的機構,持續評估治療的成本和效益,并有權阻止採用那些效益無法達到成本的治療方法。如果有一個這樣的機構來監管美國的製藥業,阿片類藥物的禍害就不會從美國蔓延出來。 更廣泛地說,不受監管的醫療保健市場對社會沒有好處。美國應該效仿其他發達國家,提供全民健康保險,并通過一個諸如NICE這樣的機構來控制醫療費用;前者很重要,而後者更重要,美國在這兩個領域都是全球最糟:然而,一旦美國政府開始干預,不但沒有控制醫療成本,而且創造了尋租的機會,這使得成本膨脹,并擴大了不平等現象。 絕望之死的危機根源在於低教育程度美國人失去了好工作,部分原因是全球化、工作外包和自動化,部分原因是醫療保健費用。工作機會的喪失破壞了許多社區,摧毀了“美式生活方式”。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支持提高工資和建立更全面社會安全網的公共政策。 資本主義需要為人服務,而不是讓人為它服務。美國不需要由國家來接管醫療保健產業,相反,美國需要的是對私營部門進行更好的監督和管理。其他發達國家有一系列處理醫療保健事業的不同方式,采取其中任何一種方式都能够改進美國的現行制度。 美國“絕望之死”的瘟疫并非不可避免,而其他發達國家也不一定能保持對這種“美國病”的免疫力。雖然目前美國只是發達國家中的“異類”,但其他國家可能也在追隨美國的腳步。如果西方國家的工資停滯不前,如果非法毒品的使用增加,美國的社會功能障礙很可能以一種普遍的方式蔓延開來,因為其他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也在努力應對全球化、工作外包和自動化的後果。“精英們繁榮昌盛,而低教育程度的工人被當作炮灰”,這種絕望之死的根源也會在其他發達國家產生類似的破壞性結果。(慧諾 譯|文化縱橫新媒體) 【編輯:豐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