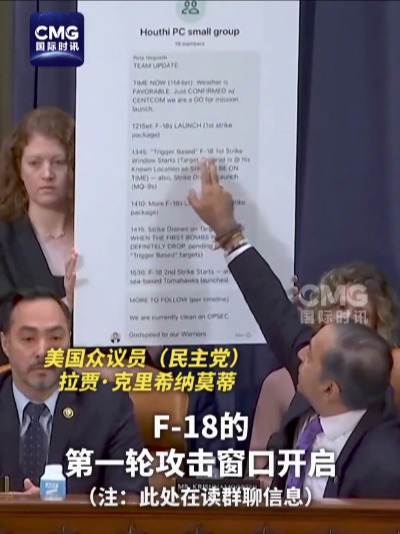【來論】劉兆佳:美歐“分道揚鑣”與世界格局的深刻調整過去幾百年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毫不誇張地說,歐洲的歷史是一部戰爭史。隨着現代國家在16世紀的興起,歐洲國家之間大大小小的戰爭多不勝數,而兩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力和殘酷性更是令人震驚。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即便東西方冷戰爆發,但歐洲在過去數十年卻因為得益於美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NATO)所發揮的保護效用,基本上能夠維持和平的狀態;而歐洲國家更能夠在經濟上一步步走向高度整合,並最終在1993年成立了全球最大和市場整合度最高的區域經濟共同體——歐盟(European Union)。 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後,歐盟和北約都陸續把一些東歐國家和部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納入其中。俄烏衝突發生後,原來拒絕參加北約的芬蘭和瑞典也最終選擇加入,令北約進一步擴大。長期以來,縱使歐洲國家之間在不少問題上比如移民、環境保護、規管和債務意見不一、齟齬叢生,但歐洲的團結卻大體上沒有受到威脅。比如,2020年英國退出歐盟雖然對歐洲的團結帶來一定衝擊,但在安全問題上英國與歐洲國家仍然維持相當合作,而彼此的合作程度又因為俄烏衝突而大為加強,所以“英國脫歐”(Brexit)對歐洲團結的影響有限。 毫無疑問,美國對二戰後歐洲的團結發揮了至關重要和不可取代的作用。如果美國不再願意維護歐洲的團結、削減對歐洲在戰略上的承擔和保證、做出損害歐洲安全和利益的行為、刻意分化歐洲國家、或者對歐洲的戰略重視程度下降,則儘管歐洲國家仍然竭盡全力維持團結,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美國大體上奉行其首任總統華盛頓的忠告,盡可能避免涉足歐洲的大國戰爭,從而維護美國的穩定和團結,以及防止美國的立國精神被玷污。一戰爆發後,由於德國一再挑釁,美國無奈參戰。戰爭結束後,儘管美國總統威爾遜(Wilson)意圖通過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來終結大國博弈,重塑國際秩序尤其是歐洲秩序以達至世界和平,但在國內孤立主義者反對插手歐洲政治下,美國卻拒絕參加該組織,遂使歐洲國家之間的衝突不但沒有止息,反而愈趨激烈,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美國亦為了阻止歐洲被德國主導而不得不再次捲入歐洲的戰爭。 二戰結束後,美國意識到自己不但不能在歐洲事務上置身事外,反而相信必須主動和積極重塑歐洲和國際秩序,方能阻止共產主義在全球擴張和危及美國的安全和利益。美國重塑歐洲秩序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經濟和政治上愈趨整合和強大的歐洲作為美國的戰略夥伴,而“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在戰後歐洲經濟重建和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協調上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歐盟的成立其實也意味着美國對歐戰略的成功。同時,美國與歐洲又構建了一個名為北約的集體安全系統,把歐洲歷史上長期交惡的國家特別是法國、德國和英國都納入其中,讓德國再難成為歐洲和平的隱患,更讓整個“西方”擁有龐大軍事力量去遏制由蘇聯領導的華沙條約組織(Warsaw Pact)。因此,毫不誇張地說,一個歷史上從未團結過的歐洲,在美國的領導、推動和“威逼利誘”下,逐步成為了一個在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上都前所未有地團結的歐洲。可以說,歐洲在二戰後之所以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與美國的介入有莫大的關係。 誠然,在過去幾十年,美國與歐洲國家乃至歐洲國家之間不時在重大問題上出現摩擦與紛爭,比如美國與英、法兩國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鬥爭,部分歐洲國家不支持美國策動的第二次海灣戰爭,美國在不知會盟友的情況下遽然倉皇撤出阿富汗,美國不時推行一些對歐洲經濟不利的貿易和貨幣政策等。有些時候,美國為了自身利益和安全考慮單方面採取行動而讓歐洲國家利益受損,比如美國在不少歐洲主要國家不同意下推動北約東擴,最後引發俄烏衝突,讓歐洲的經濟和能源安全備受打擊。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教授喬納森.哈斯蘭(Jonathan Haslam)的新書《趾高氣揚: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美國根源》(Hubris:The American Origins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2024)對此提出了有力的證據。 不過,由於歐洲在安全問題上對美國高度依賴,所以歐洲絕對不敢削弱或者割裂與美國的關係,只能逆來順受。所以,從另一角度看,正是因為有了美國的“保護傘”特別是“核子保護傘”,歐洲才得以集中精力於發展經濟和擴大福利,而歐盟亦逐漸成為美國在經濟、貿易和金融上的強大競爭對手。歐元(Euro)的誕生和其對美元霸權的挑戰,讓美國感到如芒在背。在美國的軍事保護罩下,歐洲毋須承擔沉重軍費支出,反而得以逐步孕育出一套突出和平談判、多邊主義、尊重國際法、依靠國際組織、反對戰爭、福利國家、政府在經濟發展和市場監管上的積極角色、和人權主義等的價值觀。 美國已非歐洲可信賴盟友 這套價值觀與美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背後的理念頗多拮抗之處,但在世界上卻讓歐盟擁有比美國更大的軟實力。對此,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歐洲文明教授康拉德.H.賈勞施(Konrad H. Jarausch)在其著作《陷入困境的歐洲:一種進步的替代方案》(Embattled Europe:A Progressive Alternative )(2021)中給出了生動的描述。 此外,歐洲人從來都鄙視美國,認為美國文化粗鄙不堪(uncouth),因此引起了美國人對歐洲人的不滿之情。這個現象在美國學者安德烈.S.馬爾科維茨(Andrei S. Markovits)的《粗魯的國家:歐洲為何不喜歡美國》(Uncouth Nation:Why Europe Dislikes America)(2007)一書中有精彩分析。這些事態的發展,使得美國與歐洲之間的矛盾不斷深化,但在共同打擊和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大前提下,這些矛盾也只能處於蟄伏狀態。 然而,冷戰結束後,羸弱的俄羅斯難以成為美國和歐洲的共同敵人,反而變成了他們的蔑視的累贅。在冷戰後的單極世界中,美國成為了唯一的霸主,並視全世界為它的勢力範圍,而它的戰略利益亦遍布全球。相反,歐洲則越來越聚焦在自身的發展。美歐戰略視野和目標的差異愈趨明顯,彼此的摩擦也不時發生。美國越來越把戰略重點放在亞洲,尤其是亞太地區,而遏制中國的崛起則成為了美國的戰略核心。以此之故,美國對歐洲的戰略重視度不斷下降,對承擔歐洲安全的決心和意欲亦隨之而持續減少,對維持所謂“西方”的團結的意志也逐漸萎縮。 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國著名保守派政論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其暢銷書《天堂與權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國與歐洲》(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2003)中對此轉變已經有深刻探討。他指出:“經過多年的相互怨恨和緊張之後,人們突然認識到,美國及其盟友的真正利益正在出現巨大分歧,跨大西洋關係本身也發生了變化,而且可能是不可逆轉的變化。”“後冷戰時期,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變得更加單邊主義,而與此同時,歐洲人正着手建立更加全面的國際法律體系,以遏制這種單邊主義。”“事實上,到20世紀90年代末,歐美之間實力懸殊正在微妙地撕裂跨大西洋關係的結構。美國人對歐洲盟友對其施加的限制感到不滿和不耐煩,因為這些盟友對戰爭貢獻甚微,但他們對『法律問題』的擔憂阻礙了(美國主導的)戰爭的有效進行。”卡根認為,過去美國和歐洲確實在戰略、意識形態和心理上有需要證明“西方”是一個團結的統一體,“但這種需要卻隨着柏林戰爭結束和莫斯科列寧雕像的崩塌而消失。”“由於不再需要維護和證明一個有凝聚力的『西方』的存在,美國五十年來在外交政策上的慷慨在冷戰結束後不可避免地會削弱。”“在沒有歐洲太多幫助的情況下,美國能夠做好準備並(單憑自己之力)應對世界各地的戰略挑戰嗎?答案很簡單:它已經這樣做了。” 俄烏衝突的爆發和其對美歐關係的衝擊似乎生動地印證了卡根的論斷。俄烏衝突初起時,俄羅斯因為戰略失誤而遭受挫折,而美西方則一方面對俄羅斯施加極限金融和貿易制裁,另一方面則為烏克蘭提供大量武器和裝備,務求大幅削弱俄羅斯的國力。在這場衝突中,俄羅斯固然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不過,作為一個擁有大量核武器、豐富自然資源和龐大國防工業的大國,在調整戰略後,俄羅斯在戰場上和戰略上都逐漸取得優勢,並控制了烏克蘭東部大片土地。 對美國而言,在沒有勝算下,俄烏衝突繼續下去只會對美國的利益越來越不利,而這場衝突也越來越失去美國民眾的支持。因此,特朗普再度成為美國總統後,便在“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大纛下,不顧歐洲盟友和烏克蘭的反對,單方面與俄羅斯商談結束俄烏衝突的安排。為了及早從俄烏衝突的泥潭中脫身,特朗普批評烏克蘭是衝突的始作俑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是“獨裁者”、要求烏克蘭放棄失去的領土來換取和平、逼迫烏克蘭向美國出讓利益以及迫使烏克蘭盡早舉行總統大選,否則美國便會削減乃至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美國在俄烏衝突中的立場的陡然轉變,美國突然對歐洲發起關稅戰和貿易戰,美國要求歐洲盟友大幅增加國防開支,特朗普威脅可能退出北約,特朗普對歐盟的蔑視和敵意,美國對丹麥屬地格陵蘭的覬覦,以及美國對歐洲右翼極端勢力的認可等事態,都充分顯示了美歐之間在戰略意圖、價值觀和利益上的嚴重分歧,而美歐之間的嚴重分歧復又引發了歐洲國家之間的矛盾。美歐關係也因此發生了巨變。對歐洲而言,美國不再是可以相信和依靠的盟友,在一些方面甚至是對手。美國不斷減少對歐洲的安全承擔和增加對歐洲的經濟衝擊,不但關係到歐洲的安全和發展,更關係到在美國不斷在歐洲“撤出”時,歐洲能否維持團結來應對外部挑戰和維持內部穩定。 誠然,在面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威脅”時,美國和歐洲仍然會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歐洲對美國的信任和依賴也必然會持續下降。目前和在未來一段日子,歐洲國家會在美國所能發揮團結的作用不斷減退下,積極採取政策和措施來加強歐洲的團結,尤其在安全領域。比利時根特大學(Ghent University)的馬克.德沃斯(Marc DeVos)教授在其《超級大國歐洲:歐盟的靜默革命》(Superpower Europe:The European Union's Silent Revolution)(2024)認為“歐盟正處於革命狀態。為了應對新的全球現實,從氣候危機到新冠疫情,從烏克蘭戰爭到與中國的冷戰,歐盟正在轉變為新世界秩序中的聯邦超級大國。”歐盟正在規劃從一個歐洲共同體轉變為一個歐亞國家地緣戰略聯盟,從一個價值聯盟轉變為一個權力聯盟,並將其從一個建構市場的項目轉變為一個建立國家項目。不過,種種跡象顯示,德沃斯教授對於歐洲未來的發展有點過分樂觀。 今天,在維護歐洲安全方面,部分歐洲國家提出要取代美國成為烏克蘭的主要武器提供者和安全的維護者,對俄羅斯施加更嚴厲的經濟制裁,建立獨立於美國的歐洲軍事力量,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加強歐洲與英國的軍事聯盟,法國為其他歐洲國家提供核子保護,各國團結起來抵禦美國的貿易戰等。在經濟方面,它們提出要進一步優化和整合歐洲市場,推進歐洲的科技發展和加強與非西方國家的關係。不過,歐洲各國仍然會盡力阻止美國退出北約,因為在可預見的將來歐洲難以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來保衛自己。然而,無論在安全或者經濟層面,歐洲都希望在美國對歐洲的承擔不再可靠的情況下加強歐洲的團結,讓歐洲在新的大國博弈的格局下仍能在國際事務上發揮舉足輕重作用。 但是,在美國“缺位”下,歐洲能否維持乃至加強團結仍是一個未知數。過去歐洲之所以能夠團結起來是因為各國要面對蘇聯的巨大威脅。今天,儘管俄烏衝突的出現打破了二戰後歐洲的和平和秩序,讓部分歐洲國家特別是那些前蘇聯的“衛星國”產生會否被俄羅斯“侵略”的擔憂。不過,俄烏衝突其實也暴露了俄羅斯軍事實力不足的困境,而俄羅斯的戰略意圖和能力則顯然只局限於將部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和“衛星國”納入其勢力範圍,因此很難想像俄羅斯對英國和其他主要西歐國家有領土野心。因此,對俄羅斯的擔憂難以成為團結歐洲的黏合劑。 歐洲一些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更屬多餘。這些國家批評中國在俄烏衝突中偏幫俄羅斯,為俄羅斯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和為其軍工企業供應器材和資源,因此對歐洲構成“安全威脅”。不過,這種所謂“安全威脅”能否成為團結歐洲的力量實屬疑問。很少歐洲人會相信遙遠的中國會“侵略”歐洲。事實上,歐洲與中國在經貿上關係越來越密切,而在美國的脅迫下歐洲更加依賴中國的市場和投資,所以要把中國當成“敵人”來團結歐洲根本不可能。 相反,由於美國對歐洲的一系列不友好行動導致美歐之間的摩擦不斷升溫,美國儼然成為了團結歐洲的一股力量。然而,由於歐洲對美國在安全和經濟上仍有相當程度的依賴,歐洲難以把美國當作“敵人”來團結自己,而那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和“衛星國”更不會願意與美國交惡。在“對付”美國時,那個自詡與美國有“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的英國也不會與德國和法國等國家走在一起,所以,在缺乏“生死存亡”的外來威脅的情況下,歐洲要團結起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重要的是,經過多年來的變遷,那些削弱歐洲團結的因素卻在不斷湧現。 首先,歐洲各國對來自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對自己的安全威脅有不同的評估,因此要求所有歐洲國家都大幅增加軍費支出難度不小,特別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歐洲要面對經濟和科技競爭力下降與福利開支越來越沉重的困局。如何在各國之間公平分攤歐洲軍事實力所需的費用委實不容易,更會引發彼此之間的衝突。 第二,歐洲各國在處理與美國、俄羅斯和中國關係上存在分歧。英國肯定會致力維持那個似有若無的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並藉此來擴大英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國家則會因為經濟或安全考慮有意與俄羅斯改善關係。我們更不能排除德國在俄烏衝突結束後會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強與俄羅斯的經貿關係,特別是增加俄羅斯對德國的天然氣供應來提升德國工業的競爭力。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會選擇與中國加強經貿往來。因此,歐洲要在對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立場上保持一致頗為困難。 第三,歐盟內部正面對着不少矛盾與摩擦,但卻難以通過進一步整合來有效處理,尤其在移民、經濟政策、環保和法治等問題上。歐盟在經濟上的整合程度已經相當高,但在財政政策上卻仍未一致,而要成為一個能夠在國際上縱橫捭闔的政治實體則路途仍相當遙遠。 第四,歐洲內部的右翼疑歐(Euroskeptics)勢力和各國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正在抬頭,這雖然不會導致歐盟的解體,但卻會削弱歐洲的團結。 “歐洲自主”強化中國發展機遇 第五,過去美國希望並致力於推動歐洲的團結,但近年來美國越來越視歐洲為經濟對手,因此對歐洲團結的態度轉趨消極。特朗普在其第一屆任期內,甚至鼓勵英國脫歐。我們不能排除美國日後會試圖分化歐洲各國以促進美國的利益。 第六,隨着俄烏衝突的發展對烏克蘭越來越不利,歐洲各國對烏克蘭的立場也愈趨分歧。俄烏衝突結束後,這些分歧也不會消失,甚至有擴大的可能,特別在各國如何分擔烏克蘭之後重建的費用上。 第七,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2009年的歐洲債務危機和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觸發了歐洲的內部衝突,其後遺症尚未消除。 第八,歐洲內部沒有一股強大的團結力量。法國雖然有意發揮領導作用,但國力不足。德國看似無意擔當團結歐洲的領導角色。由於德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始作俑者,其他歐洲國家對德國的疑慮尚未完全消除,它們不一定願意讓德國成為歐洲的政治領袖。 最後,西歐、南歐、東歐、中歐和北歐在經濟和政治利益上都存在分歧,這些分歧難免成為歐洲團結的障礙。 展望未來,儘管美國在團結歐洲上的角色會持續下降,歐洲仍會保持一定的團結性,但團結程度估計會有所下降。在歐洲的安全問題上,美國仍然不得不擔當一定的角色,但歐洲各國特別是德國、法國和英國卻必然會為了自身安全和利益而另闢蹊徑,從而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這尤其會展示在它們各自對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上。在外交和經貿事務上,儘管歐盟仍會繼續運作,但我估計歐洲各國的“戰略自主性”和“獨立”行動會比以前增加,而中國則可以有機會加強與歐洲乃至個別歐洲國家的關係,從而進一步擴大中國的國際活動空間和促進中國的發展。 (本文作者爲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張明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