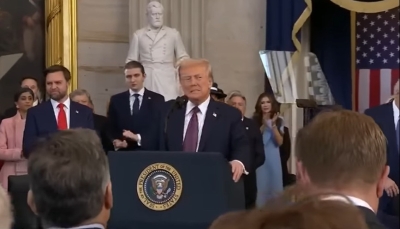名家點評《紅樓夢》人物隨著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也蓬勃發展,包蘊其中的“新文學運動”更是一往無前。時至1921年,“新紅學”應運而生,距今也已整整一百年了。 “新紅學”指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派嘗試以新的視野、史料、方法來重新研究《紅樓夢》的學術理念。“新紅學”的創立,以胡適於1921年撰述《紅樓夢考證》為標誌。可以說,“新紅學”是二十世紀紅學史上影響最大的紅學流派。胡適、顧頡剛、俞平伯等著名學者,皆為“新紅學”奠基者與開拓者;周作人、陳寅恪、吳宓等著名學者,雖未明確躋身“新紅學”陣營,可對於《紅樓夢》研究也不乏新見識,可稱廣義上的“新紅學”代表者。
《焚稿斷情圖》,清末彩繪,描繪黛玉焚毀詩稿,紫鵑在旁陪伴的情景。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首胡適題詞
尤三姐(清)改琦 繪 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這一代“新紅學”大家名師,並不是只顧史料文獻、不食人間煙火的“學神”。除卻在學術上對《紅樓夢》作者、版本、時代三個方面的字斟句酌,他們對《紅樓夢》小說本身以及小說人物,也自有一番嬉笑怒罵、性情各異的衷心品評。他們對此有著獨特的人性領悟與人生觀照,甚至於還要以《紅樓夢》人物自況自擬,把“讀後感”生生地做成了“人生觀”,把小說人物的一生真真地過成了自己的一生。
最愛“尤三姐”,最厭“林黛玉” 1929年1月3日,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由上海至杭州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第三次常會。次日上午9點,胡適參會並請辭董事一職;下午5時左右,會議便告結束。赴會之暇,胡適還參加了一次上海《鐵報》“如何評價《紅樓夢》人物”的民意測驗。 這一事跡,從未見其日記或年譜記載,更無後人提及。但這的確是見諸當年報刊的確鑿記載,並非道聽途說、添油加醋的什麽“掌故八卦”之類。這一新聞短訊篇幅不長,卻將胡適在西子湖畔參加“紅樓夢人物測驗”的事跡簡明記述了下來。胡適當時選擇的最愛者為“尤三姐”,理由是“因為她有點骨氣”,最厭者為“林黛玉”,理由則是“因為她刻薄小氣”。 胡適“最愛尤三姐,最厭林黛玉”的個人評價,也可稱一樁近代學林趣事與“紅學”逸聞。 須知,這一樁趣事與逸聞的可貴在於,一向以“史料考據”為學術旨趣的胡適,對包括《紅樓夢》在內的中國古典小說,大多只評述小說本身的版本演變史及作者生平之類,始終強調嚴謹的考證方法與縝密的史料證據鏈,鮮有直抒胸臆,直接點評小說人物之舉。這一事跡恰可證明,即使再講求客觀、理性看待文學史的學者,對待小說人物也總會有十分鮮明的主觀評價;或許可以終生不付諸論文表達,但還是有意無意地有所流露。 遺憾的是,由於記述簡短,無從獲知這一事跡的更多細節。據查,1929年的《胡適日記》於1月5日這天中斷,至10日重又開記。會議期間,他在杭州逗留了幾天,不可確考,至少兩天,卻可肯定。在這兩天之中,據其日記所載會議議程之多,他本人還兼會議秘書,恐無法抽身閑逛;與《鐵報》記者侃紅樓、填表格,更無從說起。所以,會議之後次日,即1929年1月5日與《鐵報》記者晤面的可能性較大。或者說,1月5日至9日,胡適均有在杭州逗留的可能性,這期間也皆有與《鐵報》記者晤面之可能。 事過二十年後,時至1949年4月1日,仍有此次測驗當事人對此念念不忘,又撰寫了一篇題為《胡適熱戀尤三姐》的文章,來憶述此事。文中寫道: 十五年前滬上某銀行在杭州舉行之民意測驗,列舉一問題曰:“在紅樓夢許多釵裙之中,妳最喜歡哪一位?”當時收到答案甚多,統計結果,最多人喜歡林黛玉,但在此堆疊成丘之函件,內有一封胡氏之親筆函,稱其於紅樓夢中人所喜歡者乃尤三姐,其列舉理由,稱尤三姐冷艷如冰,熱情如火,出汙泥而不染。雖難能可貴,主事者得此函後,曾大事宣傳一次,有一女讀者竟投函反問胡夫人是否喜歡柳湘蓮,惜胡夫人並未還答耳。但胡氏之熱戀尤三姐已為一時之佳話。 除了時間記憶略有疏誤之外,將二十年前的測驗誤作“十五年前”,文中提到的胡適親筆所寫“最愛尤三姐”之理由,較之《鐵報》報道者,還更為充分一些。譬如,胡適稱“尤三姐冷艷如冰,熱情如火,出汙泥而不染”雲雲,足可補充之前報道中僅稱的“因為她有點骨氣”這一句話評價。再者,此次測驗全民投票的統計結果,乃是“最多人喜歡林黛玉”,而胡適評出的“最厭林黛玉”,恰恰與“民意”相悖。 胡適這一事跡,於後世讀者而言,可視作趣事或逸聞,茶余飯後聊作談資,亦無不可。另一方面,對於所謂“紅學界”而言,“新紅學”開創者胡適的相關事跡研究已頗見規模,且早已推出《胡適紅學年譜》,這一事跡或還有“入譜”之價值。
最愛“晴雯”,最服“鳳姐” 周作人不是“紅學家”,但作為資深讀者與新文學作家,他對《紅樓夢》自有獨特評判。僅就《紅樓夢》中的小說人物品評而言,他曾明確提出過“最服鳳姐”與“最愛晴雯”的觀點。周氏曾提道:“我讀《紅樓夢》前後大約有兩三次,心裏留下的印象也還相當清楚,我所覺得佩服的只有王鳳姐,喜歡的只有晴雯。” 這一評語,出自1949年12月6日《亦報》刊發的周氏所撰文章。當時,周氏閉門讀書,心無旁騖,悠然憶述過往的讀書生涯,並將其多年的讀書心得,於筆下娓娓道來,付諸點滴文字之中。 周作人之所以這樣評判紅樓人物,乃是從“人的文學”立場出發,從小說人物創作路徑考察。他解釋稱,鳳姐與晴雯“這兩個人雖然是在榮國府大觀園裏,但是假如換上一個背景,放在城市或鄉村的平民社會裏,還是一樣的可以存在,可以發揮她的特色的”。隨後,他又進一步指出,《紅樓夢》中的人物塑造與刻畫,其原型即使在三百年後,仍然有千千萬萬的存在。換句話說,紅樓人物在後世的中國仍然大量存在,紅樓人物就是中國人人性的模板。這一觀念,周氏如此解析:“《紅樓夢》所著力的地方是描寫那些女人的性格行動,這雖是三百年前的模型,在現代也盡存在,有如那樣隨意的賈母,能幹的鳳姐,深心的寶釵,嬌性的黛玉,刁惡的襲人與率直的晴雯等,隨處可以見到一鱗半爪,這非得有社會上的大變動是不容易改變的。” 周作人始終認為,《紅樓夢》最令其佩服,也是寫得最好的人物是“王熙鳳”。他在《小說的回憶》中寫道:“正冊的二十四釵中,當然秋菊春蘭各有其美,但我細細想過,覺得曹雪芹描寫得最成功也最用力的乃是王熙鳳,她的缺點和長處是不可分的,《紅樓夢》裏的人物好些固然像是實在有過的人一樣,而鳳姐則是最活現的一個,也自然最可喜。”無論是“最活現”與“最可喜”的鳳姐,還是“野性宛然在”的晴雯,在周氏眼中,都“像是實在有過的人一樣”,這正是“人的文學”的旨趣所在,文學中的人物,必得有人情,有人性,有人味兒。
“林黛玉”不如“杜麗娘”
林黛玉(清)改琦 繪 再來看陳寅恪,早在1919年“新紅學”還沒創立之際,已近而立之年的陳氏在哈佛大學對友人吳宓講述“五等愛情論”的個人經驗。這番高論,就與《紅樓夢》中的人物有著密切聯系。 這位後來的史學大師、國學導師,以小說人物為例,把愛情分為幾個不同的層次,並把《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列於《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之後,排在了第二層,“司棋”則排在了第三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