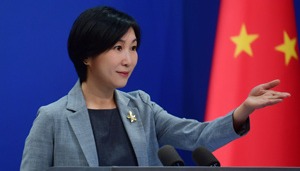香港露宿者自白:疫下兩年,我想有工開、有屋住、有飯吃香港新聞網1月23日電 時過大寒臨近年關,香港氣溫也跟著降了下來,夜風刺骨了些許。隨著通州街公園內路燈逐漸亮起,露宿者也回到了他們的“家”。 走進通州街公園,像是走入一個群體的領地,一群露宿者聚在長廊的盡頭;有人光著腳靠在墻上,看向遠方的眼神卻失了焦;也有人索性用幾片紙殼箱簡單遮身,這裡是他們為數不多的安樂窩,幾個月前年過六旬的強哥也在這裡落腳。
香港中通社圖片 “香港賺錢,內地花錢”今年60歲的強哥疫情前每日奔波兩地,香港上班、深圳生活,每月工資將近3萬港元,日子過得“不憂柴不憂米”。新冠疫情兩年,強哥多了一個新身份“回流港人露宿者”。 過往不少港人在香港工作,回內地居住,疫情後失業,內地的租金都負擔不起,因此回流的港人亦急增,惟在提供的防疫抗疫基金都未受惠,欠缺支援後成為露宿者。 強哥之前從事餐飲、建築維持生計,但疫下他無工可開,成為失業大軍一員,在內地經營的商鋪也相繼倒閉,迫於身份證過期無奈回港。百物騰貴的情況下,強哥身上的錢也所剩無幾,隨後成為“首次露宿者”露宿街頭。
香港中通社圖片 從高床暖枕頭到露宿街頭,與記者傾談間,強哥總是不住地搖頭歎氣,“生活變得很灰暗。” 露宿者最急需的是房屋。露宿數月後,在社工的幫助下,強哥已入住了露宿者宿舍。“哪裡睡得舒服就睡哪裡、哪裡安靜就睡哪裡。”紅館、文化中心、公園隧道都曾是強哥的落腳點。 目前強哥居住在6人間的“露宿者宿舍”。“現在算是‘有瓦遮頭’,不用每天早上都被人趕,晚上要很晚才能找地方睡覺。”強哥說,現在休息足夠了,精神會好點,沒有病痛才可以繼續找工作。 受疫情影響而暫時滯留香港,日後會重返內地居住,不拿綜援仍是強哥的堅持。“有散工就去做,有長工就去‘開工’,拿綜援真係好‘廢’。”他說,“拿綜援是熬日子,不是過日子。” 香港社區協會前年發布調查指,1至4月,非領綜援的露宿者出現新趨勢,不少非領綜援露宿者因為疫情而失業,六成人成為“首次露宿者”,而因疫情回流的港人急增,有部份人因為欠支援而成為露宿者。 強哥用寄人籬下形容目前處境,他坦言,過得一天得一天,待疫情好轉就會返回內地。
香港中通社圖片 目前社會福利署為露宿者提供228個緊急及短期住宿的資助宿位,連同其他非特區政府機構提供的414個自負盈虧宿位,總數合共642個宿位。 強哥僅是“首次露宿者”的縮影,能住進露宿者宿舍,他也是極度幸運的一人。但同為露宿者的阿堅就沒那麼幸運。 早年間隨父母來港,但自父母2013年回到內地後,只身留在香港的阿堅,因學徒工資無法負擔房租,開始了他長達8年斷斷續續的露宿生活,僅疫情兩年間,他就兩度露宿街頭,一個簡單的背囊裝了他全部家當。 “當時紮鐵,老闆覺得我胖蹲不下去,就辭退我了,錢又用完,只能睡街了。”通州街公園就是阿堅第一個露宿的地方,而短暫露宿僅幾個月後,他就找到長工,深水埗一間廁所臥室擠在一起的劏房成為他的家。 幾年間,阿堅的生活也頗有起色,存到了7萬港元,雖然不多,但日子也過得讓阿堅覺得滿足,那是他這幾年少有感到心安的時間。 然而好景不長,2018年的一次意外,阿堅傷了腳,因為不是工傷,只能自費治療,病來如山倒,短短一年他就花光了所有積蓄,租房還是吃飯成為兩難抉擇,疫情前夕他第二次開始露宿。 “第一次很難接受自己成為露宿者,後來睡街多了,也就能稍稍接受了。”幾年來阿堅一直都想擺脫露宿者的身份,養好腳傷後,他立馬開始找工作,手裡有了餘錢,他住上了宿舍,眼看著生活向好的阿堅,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一次重擊。 2020年1月23日農曆新年剛過,香港出現首宗新冠確診個案,接下來數月間,阿堅從事的裝修行業也受到衝擊,他再次成為露宿者。從春夏到秋冬,露宿的日子可想而知不好過,“夏天在公園睡,有風涼快些,冬天就凍一些。” 疫情兩年,阿堅明顯感覺到“休息太久,沒工作,身體都不好了。跌壞腳時很傷心,因為好不容易有錢又花沒了,但這兩年沒什麼開心的,但也沒那麼傷心。” 隧道、公園居無定所的兩年間,“家”是阿堅內心最渴望的地方。“你有什麼目標嗎?”被問及未來,阿堅不停搓手顯得十分侷促,露宿生活讓原本不多言的阿堅更為內向,短暫思考一下,阿堅說,“我現在打算找個長工,每個月交得起3000塊房租,吃得起飯,就行了。”
香港中通社圖片 晚上近8時,通州街公園附近已人跡寥寥,幾百米開外高檔住宅為公園擋去了些許寒風,暫居這裡的露宿者也已各自尋個地方靜下來,在路燈下睡去,他們還要在第二天清晨前離開。(李明珠 崔靜雯) 【編輯:李明珠】
|